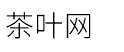于茶香處與茶相處
發布時間:2025-09-07 點擊:28
近來,愛于周末往南橋寺跑,和幾個老同學一起。
南橋寺有號稱重慶最大的茶葉市場,其間茶葉、茶具及各色茶用品齊備,各人視腰包狀況而定,幾乎都能選擇到自己的需要甚至所愛。老同學都有快30年的交情了,當年圍坐一處,捧一只因不知愛惜而破舊的搪瓷缸,就著半溫不熱的暖水瓶,泡出忽濃忽淡的下關沱茶,時而苦澀、時而甘甜,如同當時少年。
如今,下關沱茶的身價已暴漲了數十倍,而我們增添的不過是兩鬢白發,雖然我們不再以搪瓷缸待客,也開始注重把握沖泡的技巧,甚至為了所謂真正的味道而玩弄起器具和技巧,但茶的味道其實已悄然改變。
巴蜀之地多陰霾,故有蜀犬吠日的典故。巴蜀之人為去濕氣,卻又不舍飲食辛辣,乃以飲茶調和。成都平原物產豐饒,民生富裕,于是蜀中曾有“村村佛寺、處處茶室”的美景。重慶氣候極端,茶風也甚。家中曾有一長輩,退休后在家含飴弄孫,老人家每天第一泡好茶,一定要等兩三歲的孫兒起床后同飲,幾年下來,小孩已是無茶不歡,我曾經在拜訪時見到他剛放小學歸來,抱著茶杯,靜坐一旁聽大人說事兒的樣子,驚嘆不已。
近些年來,重慶人和成都人一直較著勁,持續了兩地孰優孰劣的一場口水大戰。在眾多媒體的介入下,一些原本沒有可比性的對比,被很多從未在對方地區生活過的人們津津樂道,讓我這種對成都的閑適、溫潤充滿懷念的重慶人只好噤言,不敢稍有造次。
我在成都讀大學時算不算好學生自己不好下結論,但對老夫子的枯燥說教忍無可忍時,也時常越墻來到隔壁公園竹林深處的茶館,對著三毛錢一客的茉莉蓋碗,或與同窗高談闊論,或于一隅昏昏欲睡,或于苦讀的書卷里拾起目光,細辨著竹葉間漏下的陽光,究竟有幾縷正逐漸昏黃;茶香浮動,詩書漫卷,時而竟以為到了老師未能解說的意境。多年以后,同學們在成都見面,仍然喜歡相約望江樓下、薛濤井旁的老茶館,這時,茶也承載了幾分別樣的濃情。
而兒時的重慶,夏日炎炎,城中到處都是賣茶人。當時七分錢一瓶的汽水絕對是奢侈品,普通人多是喝一分錢一碗的“老蔭茶”。我至今也沒有搞清楚這究竟是一種什么茶,它似乎是其他樹種的葉子,并非真正的茶樹葉。
重慶是山城,還是火爐,夏日里烈日當空,酷熱無比。但無論城里城外,當你艱難地爬上一段陡峭的青石板路,只要有陰涼的地方,往往就有老蔭茶攤。許多茶攤就擺在濃蔭如蓋的黃桷樹下,兩只木桶,幾只小凳,而當你坐下身來,痛飲一氣,焦渴盡去,擺攤的老人還會遞上一把破舊的蒲扇,一陣緊搖慢晃之后,有清風徐徐自樹上而下。炎夏的午后,萬眾悄聲,唯有蟬鳴,攤前攤外兩重天。至于茶與非茶,已然兩忘。
有幾年我曾生活在長沙,深感其民間的待客茶道特殊。當地人用炒熟的芝麻、糯米、花生、核桃等,加上上好的洞庭碧螺春混泡,那又是另一番滋味。特別是主人喝完茶湯以后,彎著小指認真地把杯中所有的東西慢慢掏起,倒入口中細細咀嚼的樣子,讓我至今難忘。茶香、米香、瓜仁香,口中溢滿洞庭魚米鄉的富足,讓人盡享歡愉,其間樂也融融,主客于是盡歡。
但在長沙我真正喝到的好茶,卻是正宗的福建大紅袍。一群天南海北的年輕人匯聚于軍校任教,我來自巴蜀,每次探家后回長沙必帶上兩瓶五糧液犒勞兄弟。雖然酒是我們一起喝的,但作為回饋,兩個福建籍的同事每次都回贈我兩聽大紅袍。那個時候喝綠茶的人多,許多人不習慣大紅袍濃烈如酒的風格,我樂得一個人獨享。照著書上介紹的樣子,買齊了正宗宜興紫砂杯壺盞,時常于夜靜時分,悄然一杯一壺,伴一桌一燈,獨自品茶。
軍校的夜晚有燈火管制,早早的,四下里已是寂靜無聲。我于座前,不讀不思,不眠不醒,恍惚間,看茶煙暗起,茶湯在紫砂的襯托下,流溢著深褐色的光輝,與暗夜同趣,卻于慢飲細品之間,轉換著甘與苦、澀與甜的變幻,宛如這靜夜里的眾生,無論夢醒,都平復了急切與躁動,屏住了歡笑與哭泣,在暗夜中寄望著明天,在絕望中等待著希望。
今天要想買到上好的傳統制法的大紅袍已非易事,個中原因,連茶市那些店里的小姑娘都心時明了。商人逐利,無可厚非,只是苦了愛茶之人。茶與茶是,茶與茶非,世事滄桑,竟至于此,奈何?
于是想起和一個朋友的一次爭論。
某天酒勁上頭,指著在座一位愛好書法的朋友求字,朋友問寫什么,我隨口答道:“茶煙起處、坐而忘憂”。卻不知朋友立刻正色告我,需改成“懷憂”二字才肯磨墨,并情真意切地教導了我一番,諸如職業、職責之類。范仲淹當年一句“江湖廟堂”的排比句,竟被朋友用來作為教訓我的依據,這是當年我登岳陽樓時萬萬沒想到的。
20年前一個夏天的下午,風雨交加,我偶然登上了岳陽樓。危欄之外,浩渺洞庭陰云密布,極目遠望,對面君山渺無影跡。此時把玩著手中的茶杯,只見杯中銀針顆顆懸立,碧綠的葉片上白毫點點,如新竹掛著黎明的春雨。天色尚早,身邊游人如織,因為使用統一的教科書,天下人幾乎沒有不知岳陽樓的,聽著身邊各色口音誦讀著范老的名篇,遙望著對面因風浪四起而不可登臨的君山,我忽然發現,杯中的銀針更像瀟湘幽怨的斑竹葉,平淡清洌,暗懷幽香,只不知是否有人嘗出過眼淚的味道?
天下茶葉,各有其種,我沒有上好的機緣,不能遍嘗天下名茶,不過并不遺憾。茶雖有異,但也相通,知其一,即可管窺其他。天下好茶有其共性:須在一定高的海拔、一定量的水汽之地,方能產出。“揚子江中水,蒙頂山上茶”,如今臺灣人賣烏龍,必稱采于凍頂之上。阿里山終年云霧繚繞,茶雖成林,飄渺間卻無浮世之喧,葉屬新發,揉捻后卻滋味綿長。茶雖俗物,竟然有品嗎?
年初陪單位里的幾位老同志踏青,偶然進了深山中一座不起眼的小廟,主持師太拿出自己采制的新茶待客,用的是一套正宗的功夫茶茶具。師太年齡不大,自我介紹大學畢業后在南粵工作,后來出了家。其后許下宏愿,來此地欲光大這個曾經輝煌而今早已破敗的寺院。
出家人事,我等不便多問。在她絮絮的介紹中,我只見午后的陽光,透過小廟土墻上腐朽但潔凈的窗欞,灑在她灰色的衣服上,使這樸素的布衣,平添了一分近乎神圣的色彩。新茶是師太第一次學著采制的,入口既苦又澀,但我們每一個人都認真喝完了她遞上的每一泡茶湯。臨走時,不忘祝她心想事成,如愿以償。
茶本無品,其品在人。如今盛世,茶市興旺,茶色種種,可任君挑。在我,則是量力而行,取其中一二而已。一年多來,因工作原因,時常獨處,于是在宿舍里配了一套還算hifi的音響,置了一套用得上手的茶具,閑來無事,開壺投茶,把杯覓香;聽爵士、古典、器樂、人聲,無論中外古今有名無名,全然因當時心情信馬由韁。偶爾有朋友來訪,也只以清茶相奉,待人去后,月冷杯空,剛才茶人茶事、眼前舊時景物,皆似是而非,我仍于茶香處,與茶相處。
當此之時,何為喜、何為憂?
南橋寺有號稱重慶最大的茶葉市場,其間茶葉、茶具及各色茶用品齊備,各人視腰包狀況而定,幾乎都能選擇到自己的需要甚至所愛。老同學都有快30年的交情了,當年圍坐一處,捧一只因不知愛惜而破舊的搪瓷缸,就著半溫不熱的暖水瓶,泡出忽濃忽淡的下關沱茶,時而苦澀、時而甘甜,如同當時少年。
如今,下關沱茶的身價已暴漲了數十倍,而我們增添的不過是兩鬢白發,雖然我們不再以搪瓷缸待客,也開始注重把握沖泡的技巧,甚至為了所謂真正的味道而玩弄起器具和技巧,但茶的味道其實已悄然改變。
巴蜀之地多陰霾,故有蜀犬吠日的典故。巴蜀之人為去濕氣,卻又不舍飲食辛辣,乃以飲茶調和。成都平原物產豐饒,民生富裕,于是蜀中曾有“村村佛寺、處處茶室”的美景。重慶氣候極端,茶風也甚。家中曾有一長輩,退休后在家含飴弄孫,老人家每天第一泡好茶,一定要等兩三歲的孫兒起床后同飲,幾年下來,小孩已是無茶不歡,我曾經在拜訪時見到他剛放小學歸來,抱著茶杯,靜坐一旁聽大人說事兒的樣子,驚嘆不已。
近些年來,重慶人和成都人一直較著勁,持續了兩地孰優孰劣的一場口水大戰。在眾多媒體的介入下,一些原本沒有可比性的對比,被很多從未在對方地區生活過的人們津津樂道,讓我這種對成都的閑適、溫潤充滿懷念的重慶人只好噤言,不敢稍有造次。
我在成都讀大學時算不算好學生自己不好下結論,但對老夫子的枯燥說教忍無可忍時,也時常越墻來到隔壁公園竹林深處的茶館,對著三毛錢一客的茉莉蓋碗,或與同窗高談闊論,或于一隅昏昏欲睡,或于苦讀的書卷里拾起目光,細辨著竹葉間漏下的陽光,究竟有幾縷正逐漸昏黃;茶香浮動,詩書漫卷,時而竟以為到了老師未能解說的意境。多年以后,同學們在成都見面,仍然喜歡相約望江樓下、薛濤井旁的老茶館,這時,茶也承載了幾分別樣的濃情。
而兒時的重慶,夏日炎炎,城中到處都是賣茶人。當時七分錢一瓶的汽水絕對是奢侈品,普通人多是喝一分錢一碗的“老蔭茶”。我至今也沒有搞清楚這究竟是一種什么茶,它似乎是其他樹種的葉子,并非真正的茶樹葉。
重慶是山城,還是火爐,夏日里烈日當空,酷熱無比。但無論城里城外,當你艱難地爬上一段陡峭的青石板路,只要有陰涼的地方,往往就有老蔭茶攤。許多茶攤就擺在濃蔭如蓋的黃桷樹下,兩只木桶,幾只小凳,而當你坐下身來,痛飲一氣,焦渴盡去,擺攤的老人還會遞上一把破舊的蒲扇,一陣緊搖慢晃之后,有清風徐徐自樹上而下。炎夏的午后,萬眾悄聲,唯有蟬鳴,攤前攤外兩重天。至于茶與非茶,已然兩忘。
有幾年我曾生活在長沙,深感其民間的待客茶道特殊。當地人用炒熟的芝麻、糯米、花生、核桃等,加上上好的洞庭碧螺春混泡,那又是另一番滋味。特別是主人喝完茶湯以后,彎著小指認真地把杯中所有的東西慢慢掏起,倒入口中細細咀嚼的樣子,讓我至今難忘。茶香、米香、瓜仁香,口中溢滿洞庭魚米鄉的富足,讓人盡享歡愉,其間樂也融融,主客于是盡歡。
但在長沙我真正喝到的好茶,卻是正宗的福建大紅袍。一群天南海北的年輕人匯聚于軍校任教,我來自巴蜀,每次探家后回長沙必帶上兩瓶五糧液犒勞兄弟。雖然酒是我們一起喝的,但作為回饋,兩個福建籍的同事每次都回贈我兩聽大紅袍。那個時候喝綠茶的人多,許多人不習慣大紅袍濃烈如酒的風格,我樂得一個人獨享。照著書上介紹的樣子,買齊了正宗宜興紫砂杯壺盞,時常于夜靜時分,悄然一杯一壺,伴一桌一燈,獨自品茶。
軍校的夜晚有燈火管制,早早的,四下里已是寂靜無聲。我于座前,不讀不思,不眠不醒,恍惚間,看茶煙暗起,茶湯在紫砂的襯托下,流溢著深褐色的光輝,與暗夜同趣,卻于慢飲細品之間,轉換著甘與苦、澀與甜的變幻,宛如這靜夜里的眾生,無論夢醒,都平復了急切與躁動,屏住了歡笑與哭泣,在暗夜中寄望著明天,在絕望中等待著希望。
今天要想買到上好的傳統制法的大紅袍已非易事,個中原因,連茶市那些店里的小姑娘都心時明了。商人逐利,無可厚非,只是苦了愛茶之人。茶與茶是,茶與茶非,世事滄桑,竟至于此,奈何?
于是想起和一個朋友的一次爭論。
某天酒勁上頭,指著在座一位愛好書法的朋友求字,朋友問寫什么,我隨口答道:“茶煙起處、坐而忘憂”。卻不知朋友立刻正色告我,需改成“懷憂”二字才肯磨墨,并情真意切地教導了我一番,諸如職業、職責之類。范仲淹當年一句“江湖廟堂”的排比句,竟被朋友用來作為教訓我的依據,這是當年我登岳陽樓時萬萬沒想到的。
20年前一個夏天的下午,風雨交加,我偶然登上了岳陽樓。危欄之外,浩渺洞庭陰云密布,極目遠望,對面君山渺無影跡。此時把玩著手中的茶杯,只見杯中銀針顆顆懸立,碧綠的葉片上白毫點點,如新竹掛著黎明的春雨。天色尚早,身邊游人如織,因為使用統一的教科書,天下人幾乎沒有不知岳陽樓的,聽著身邊各色口音誦讀著范老的名篇,遙望著對面因風浪四起而不可登臨的君山,我忽然發現,杯中的銀針更像瀟湘幽怨的斑竹葉,平淡清洌,暗懷幽香,只不知是否有人嘗出過眼淚的味道?
天下茶葉,各有其種,我沒有上好的機緣,不能遍嘗天下名茶,不過并不遺憾。茶雖有異,但也相通,知其一,即可管窺其他。天下好茶有其共性:須在一定高的海拔、一定量的水汽之地,方能產出。“揚子江中水,蒙頂山上茶”,如今臺灣人賣烏龍,必稱采于凍頂之上。阿里山終年云霧繚繞,茶雖成林,飄渺間卻無浮世之喧,葉屬新發,揉捻后卻滋味綿長。茶雖俗物,竟然有品嗎?
年初陪單位里的幾位老同志踏青,偶然進了深山中一座不起眼的小廟,主持師太拿出自己采制的新茶待客,用的是一套正宗的功夫茶茶具。師太年齡不大,自我介紹大學畢業后在南粵工作,后來出了家。其后許下宏愿,來此地欲光大這個曾經輝煌而今早已破敗的寺院。
出家人事,我等不便多問。在她絮絮的介紹中,我只見午后的陽光,透過小廟土墻上腐朽但潔凈的窗欞,灑在她灰色的衣服上,使這樸素的布衣,平添了一分近乎神圣的色彩。新茶是師太第一次學著采制的,入口既苦又澀,但我們每一個人都認真喝完了她遞上的每一泡茶湯。臨走時,不忘祝她心想事成,如愿以償。
茶本無品,其品在人。如今盛世,茶市興旺,茶色種種,可任君挑。在我,則是量力而行,取其中一二而已。一年多來,因工作原因,時常獨處,于是在宿舍里配了一套還算hifi的音響,置了一套用得上手的茶具,閑來無事,開壺投茶,把杯覓香;聽爵士、古典、器樂、人聲,無論中外古今有名無名,全然因當時心情信馬由韁。偶爾有朋友來訪,也只以清茶相奉,待人去后,月冷杯空,剛才茶人茶事、眼前舊時景物,皆似是而非,我仍于茶香處,與茶相處。
當此之時,何為喜、何為憂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