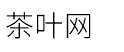個人對于吃茶的興趣
發布時間:2025-10-08 點擊:24
茶這樣東西,雖然不如衣食之重要,但它總是人們生活上不可一日或缺之物,所以古來的媽媽經濟家,也把它列入開門七件事之一。而飲食兩字又聯成一個名詞,并且“飲”還在“食”之上。則其重要,實在不遜于衣食。詩人的“寒夜客來茶當酒”,的是名句,不特境界清幽,趣致亦高雅。又昔日文人詩文中,以詠酒記茶之篇最多,我想這是時代的不同,到后來便以煙代替了酒。我個人也是喜歡這兩樣,而不大喝酒的。尤其是好煙佳茗,無論是花晨月夕,也不管是春風秋雨,都可以慰人寂寥,沁人心脾。
不過近來紙煙缺乏,不大好買,而我又是懶得成隨遇而安的人,有時候在“二者不可得兼”的環境下,于是茶更顯其重要。真是“誰謂茶(荼改)苦,其甘如薺”。故平常每當一張(報)在手一枝(煙)在口的時候,這一杯好茶的需要,比任何事物還要迫切。這種嗜好,我想世人中總不在少數吧。
吃茶說雅一點便是品茗,雖然是件日常的普通事,但這里面也有很多的講究,極專門的學問。所以關于“茶經”,“茶典”,“茶史”等那一套,都暫且不想提他,只是談談我個人對于吃茶的興趣罷了。
我覺得茶,它的好處,也可說是它的長處,便是無論在什么場所,它都可以與思慮、情感融化,決不隨主觀而有喜厭。譬如我在上海的時候,常常同朋友到永安茶室去吃茶。雖然那個地方是繁華中樞,那個所在是洋樓大廈,吃茶的時候,又只見一片人海,萬頭攢動,且市聲嘈雜。但與二三知己,上下古今,高談闊論。鬧中取靜,以絢爛為平淡。一杯清茗,反覺得悠閑舒適。古人說:“臣門如市,臣心似水。”頗可于此借用。
所以在熱鬧的地方吃茶,也不失其清幽。至于久居北京,自然以公園之地最雅,茶最新,松柏參天,花葉滿地,樹下品茗,頓覺胸襟開朗,塵俗全消。而紅男綠女,雅士高人,土氣粉香,襲人眼鼻,身坐園林,特感幽趣。論其境界,一動一靜,雖不必說有高下之分,實在有老少之別。因為在精神上,好像一個是摩登少年的,一個是澹靜老年的。
還有他的功用,就是調劑疲勞,除了吃茶以外,沒有再好的方法。所以常看見北平的車夫,每逢走到有名的茶葉店門前,總是進去買一包“高末”(好茶葉末兒),預備回頭休息的時候養養神。因此它能夠普及的原因,便是同紙煙一樣,沒有階級性。不像雪茄煙,老是拿在富貴人的手中,平常的人拿著,與身份也不大調協。有點“鼻子大了壓倒嘴”的神氣。
關于論茶的文章,雖然很多,但大都偏于煮茶與茶具方面,明人言之尤詳,李漁的《閑情偶寄?一家言》即其代表。而說得較深刻有趣致者,還是文震亨的《長物志》,其卷十二香茗云:“香茗之用,其利最溥。物外高隱,坐語道德,可以清心悅神。初陽薄暝,興味蕭騷,可以暢懷舒嘯。晴窗榻帖,揮麈閑吟,篝燈夜讀,可以遠辟睡魔。青衣紅袖,密語談私,可以助情熱意。坐雨閉窗,飯余散步,可以遣寂除煩。醉筵醒客,夜語蓬窗,長嘯空樓,冰弦戛指,可以佐歡解渴。品之最優者,以沉香芥茶為首,第焚煮有法,必貞夫韻士,乃能究心耳。”這段雖然以“香”與“茗”,同時描寫,而香究屬于氣味,虛無縹緲,故仍著重茶字,以香作陪襯耳。
至于講論吃茶,似以陳金詔《觀心室筆談》所述,最為可取。他說:“茶色貴白,白亦不難,泉清瓶潔,旋烹旋啜,其色白白。若極嫩之碧螺春,烹以雨水文火,貯壺長久,其色如玉。冬猶嫩綠,味甘香清,純是一種太和元氣,沁入心脾,使人之意也消。”又云:“茶壺以小為貴,每一客一壺,任獨斟獨飲,方得茶趣。何也,壺小香不渙散,味不耽遲,不先不后,恰有一時,太早不足,稍緩已過,個中之妙,以心受者自知。又云:“茶必色香味三者俱全,而香清味鮮,更入精微。須真賞深嗜者之性情,從心肺間一一淋漓而出。”
以上各條,由平淡中深得妙諦,知作者于吃茶一事,可謂三折肱矣。陳氏又淪茶云:“江南之茶,唐人首稱陽羨,宋人最重建州。近日所尚者,惟天目之龍井。蓋所產之地,朝光夕暉,云滃霧浮,醞釀清純,其味迥別,疑即古之顧渚紫筍也。要不若洞庭之碧螺春,韻致清遠,滋味甘香,全受風露清虛之氣,可稱仙品。”按陳氏為清道咸間人,故他的高論,與我們的見聞,尚不相差太遠,也能作會心的領悟。不似明以前的文章,無論如何精辟,于時代上,總覺得隔一層似的。
又吃茶遺事,清乾嘉時破額山人《夜航船》記“絳囊三品”:“偶閱宋史天禧末年,天下茶皆禁止,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。自后定法,務從輕減。太平興國二年,主吏盜官茶販鬻【yù】錢三貫以上,黔面送闕下。歐陽文忠公上奏:往時官茶容民入雜,故茶多。今民自買賣,須要真茶,真茶不多,其價遂貴。予想今若此渴殺人矣。葉生在旁曰:我與君無礙,菖蒲汁橄欖湯,亂嚼檳榔木,盡可應酬涸舌。所苦者眉生耳。眉生者進士新淦令莼卿公次子,酷嗜茗茶者也。生嘗曰:茗茶味苦,益人知慮不淺。
座右書一聯云:‘身健卻緣餐飯少,詩清每為飲茶多。’喜硯石;善清談,麈揮玉映,香屑霏霏,竟易厭。遇龍圖,雀舌、蒙頂、日鑄,則漱口汩汩,枯腸沃透,若清明后勿潤喉也,谷雨后勿沾唇也。每造友家,輒自帶茶,恐主人茶不佳也。主人艷其茶好,恒與索之。于是座客盡索之,生窘甚。
歸家制絳紗囊三枚,上囊曰原,中囊曰法,下囊曰具,依陸鴻漸《茶經》三篇之名而名之。上系領上,中系肘后,下系腰間。上貯絕妙佳品,非原原本本,殫見博聞,兼詩骨高超,功深養邃,有益于己者,不得丐其余瀝。若胸無城府,語亦中聽,可以中囊之法字號與飲。然已不可多得。目前泛泛之交,下囊應酬而已。”
眉生名士,雖然懂茶,未免把茶看得太珍惜一點,還是隨便些聽其自然,則更有逸趣。于上記可知“官茶”容民入雜。民自買賣,始得真茶,但價亦貴。這與今天的配給相似,凡是所謂“官米”,“官面”,“官煙”,“官糖”,總是有假。自由買賣的,價錢又貴。真是自古已然,于今為烈了。
還有一種吃茶的方式,于時間上地理上,都稱得起上乘,便是鄉間的“野茶館”。只可惜都會的人們,少有機會去享受。所謂野茶館,在北京大半都在城外,或依古寺,或近村莊,有臨時搭棚的,有于屋前藤蘿花架下,取自然環境的。座位不多,天然幽靜。尤其大清早晨,紅日未升,余露猶濕,鳥語花香,氣新神爽。
凡來“溜彎”吃茶的養鳥的人,將鳥籠掛于檐前,讓它去“調嗓”,引吭高歌。自己一面啜茗,一面和同道或談些市井瑣事,或講些社會新聞。真可說是世外桃源,羲皇上人。我以為這種境界,與“楊柳岸曉風殘月”的圖畫實相仿佛。城里雖然有什剎海,也可以臨水看荷,但終不是農田鄉下。越是久居城市的人,越感覺得這種地方悠閑無為的可貴與可愛。
末了附帶的說到“茗具”,自明以來,便一致公認以砂壺為最合適。李笠翁《一家言》,有茶具一篇,他說:“茶注莫妙于砂壺,砂壺之精者,又莫過于陽羨。又云:凡制茗壺,其嘴務直,一曲便可憂,再曲則稱棄物矣。……星星之葉,入水即成大片。啜茗快事,斟之不出,大覺悶人。”李氏所談,可謂快語。
清中葉以后,砂壺之中,又重陳曼生(鴻壽)所制,名為“曼壺”。確較一般精雅別致。不過近來曼壺真者,頗不易得,即有價亦昂貴。日前在隆福寺古玩攤上,見有小砂壺一具,質式均極精巧,一入眼即知其必系名作,壺底果有“宣統元年匋齋自制”篆章,惜壺蓋略有殘缺,乃用漿糊粘合者。嫌其破損,太息而去。
返家后于心耿耿,終不能釋。乃于第二日亟【jí】去尋購,據云余看后即出手矣。按匋齋系清人端方號,端方好收藏古物。辛亥革命前,在四川被殺,其枕匣中只一部舊抄本《紅樓夢》。可見好東西自有識者。余所置雖有砂壺數件,而日用者仍為瓷壺。老實說還是沒有這種真正的閑心逸情,所以雖然天天吃茶,而沒有一次品茗。所謂品的環境與機會,也確是很難得的。
不過近來紙煙缺乏,不大好買,而我又是懶得成隨遇而安的人,有時候在“二者不可得兼”的環境下,于是茶更顯其重要。真是“誰謂茶(荼改)苦,其甘如薺”。故平常每當一張(報)在手一枝(煙)在口的時候,這一杯好茶的需要,比任何事物還要迫切。這種嗜好,我想世人中總不在少數吧。
吃茶說雅一點便是品茗,雖然是件日常的普通事,但這里面也有很多的講究,極專門的學問。所以關于“茶經”,“茶典”,“茶史”等那一套,都暫且不想提他,只是談談我個人對于吃茶的興趣罷了。
我覺得茶,它的好處,也可說是它的長處,便是無論在什么場所,它都可以與思慮、情感融化,決不隨主觀而有喜厭。譬如我在上海的時候,常常同朋友到永安茶室去吃茶。雖然那個地方是繁華中樞,那個所在是洋樓大廈,吃茶的時候,又只見一片人海,萬頭攢動,且市聲嘈雜。但與二三知己,上下古今,高談闊論。鬧中取靜,以絢爛為平淡。一杯清茗,反覺得悠閑舒適。古人說:“臣門如市,臣心似水。”頗可于此借用。
所以在熱鬧的地方吃茶,也不失其清幽。至于久居北京,自然以公園之地最雅,茶最新,松柏參天,花葉滿地,樹下品茗,頓覺胸襟開朗,塵俗全消。而紅男綠女,雅士高人,土氣粉香,襲人眼鼻,身坐園林,特感幽趣。論其境界,一動一靜,雖不必說有高下之分,實在有老少之別。因為在精神上,好像一個是摩登少年的,一個是澹靜老年的。
還有他的功用,就是調劑疲勞,除了吃茶以外,沒有再好的方法。所以常看見北平的車夫,每逢走到有名的茶葉店門前,總是進去買一包“高末”(好茶葉末兒),預備回頭休息的時候養養神。因此它能夠普及的原因,便是同紙煙一樣,沒有階級性。不像雪茄煙,老是拿在富貴人的手中,平常的人拿著,與身份也不大調協。有點“鼻子大了壓倒嘴”的神氣。
關于論茶的文章,雖然很多,但大都偏于煮茶與茶具方面,明人言之尤詳,李漁的《閑情偶寄?一家言》即其代表。而說得較深刻有趣致者,還是文震亨的《長物志》,其卷十二香茗云:“香茗之用,其利最溥。物外高隱,坐語道德,可以清心悅神。初陽薄暝,興味蕭騷,可以暢懷舒嘯。晴窗榻帖,揮麈閑吟,篝燈夜讀,可以遠辟睡魔。青衣紅袖,密語談私,可以助情熱意。坐雨閉窗,飯余散步,可以遣寂除煩。醉筵醒客,夜語蓬窗,長嘯空樓,冰弦戛指,可以佐歡解渴。品之最優者,以沉香芥茶為首,第焚煮有法,必貞夫韻士,乃能究心耳。”這段雖然以“香”與“茗”,同時描寫,而香究屬于氣味,虛無縹緲,故仍著重茶字,以香作陪襯耳。
至于講論吃茶,似以陳金詔《觀心室筆談》所述,最為可取。他說:“茶色貴白,白亦不難,泉清瓶潔,旋烹旋啜,其色白白。若極嫩之碧螺春,烹以雨水文火,貯壺長久,其色如玉。冬猶嫩綠,味甘香清,純是一種太和元氣,沁入心脾,使人之意也消。”又云:“茶壺以小為貴,每一客一壺,任獨斟獨飲,方得茶趣。何也,壺小香不渙散,味不耽遲,不先不后,恰有一時,太早不足,稍緩已過,個中之妙,以心受者自知。又云:“茶必色香味三者俱全,而香清味鮮,更入精微。須真賞深嗜者之性情,從心肺間一一淋漓而出。”
以上各條,由平淡中深得妙諦,知作者于吃茶一事,可謂三折肱矣。陳氏又淪茶云:“江南之茶,唐人首稱陽羨,宋人最重建州。近日所尚者,惟天目之龍井。蓋所產之地,朝光夕暉,云滃霧浮,醞釀清純,其味迥別,疑即古之顧渚紫筍也。要不若洞庭之碧螺春,韻致清遠,滋味甘香,全受風露清虛之氣,可稱仙品。”按陳氏為清道咸間人,故他的高論,與我們的見聞,尚不相差太遠,也能作會心的領悟。不似明以前的文章,無論如何精辟,于時代上,總覺得隔一層似的。
又吃茶遺事,清乾嘉時破額山人《夜航船》記“絳囊三品”:“偶閱宋史天禧末年,天下茶皆禁止,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。自后定法,務從輕減。太平興國二年,主吏盜官茶販鬻【yù】錢三貫以上,黔面送闕下。歐陽文忠公上奏:往時官茶容民入雜,故茶多。今民自買賣,須要真茶,真茶不多,其價遂貴。予想今若此渴殺人矣。葉生在旁曰:我與君無礙,菖蒲汁橄欖湯,亂嚼檳榔木,盡可應酬涸舌。所苦者眉生耳。眉生者進士新淦令莼卿公次子,酷嗜茗茶者也。生嘗曰:茗茶味苦,益人知慮不淺。
座右書一聯云:‘身健卻緣餐飯少,詩清每為飲茶多。’喜硯石;善清談,麈揮玉映,香屑霏霏,竟易厭。遇龍圖,雀舌、蒙頂、日鑄,則漱口汩汩,枯腸沃透,若清明后勿潤喉也,谷雨后勿沾唇也。每造友家,輒自帶茶,恐主人茶不佳也。主人艷其茶好,恒與索之。于是座客盡索之,生窘甚。
歸家制絳紗囊三枚,上囊曰原,中囊曰法,下囊曰具,依陸鴻漸《茶經》三篇之名而名之。上系領上,中系肘后,下系腰間。上貯絕妙佳品,非原原本本,殫見博聞,兼詩骨高超,功深養邃,有益于己者,不得丐其余瀝。若胸無城府,語亦中聽,可以中囊之法字號與飲。然已不可多得。目前泛泛之交,下囊應酬而已。”
眉生名士,雖然懂茶,未免把茶看得太珍惜一點,還是隨便些聽其自然,則更有逸趣。于上記可知“官茶”容民入雜。民自買賣,始得真茶,但價亦貴。這與今天的配給相似,凡是所謂“官米”,“官面”,“官煙”,“官糖”,總是有假。自由買賣的,價錢又貴。真是自古已然,于今為烈了。
還有一種吃茶的方式,于時間上地理上,都稱得起上乘,便是鄉間的“野茶館”。只可惜都會的人們,少有機會去享受。所謂野茶館,在北京大半都在城外,或依古寺,或近村莊,有臨時搭棚的,有于屋前藤蘿花架下,取自然環境的。座位不多,天然幽靜。尤其大清早晨,紅日未升,余露猶濕,鳥語花香,氣新神爽。
凡來“溜彎”吃茶的養鳥的人,將鳥籠掛于檐前,讓它去“調嗓”,引吭高歌。自己一面啜茗,一面和同道或談些市井瑣事,或講些社會新聞。真可說是世外桃源,羲皇上人。我以為這種境界,與“楊柳岸曉風殘月”的圖畫實相仿佛。城里雖然有什剎海,也可以臨水看荷,但終不是農田鄉下。越是久居城市的人,越感覺得這種地方悠閑無為的可貴與可愛。
末了附帶的說到“茗具”,自明以來,便一致公認以砂壺為最合適。李笠翁《一家言》,有茶具一篇,他說:“茶注莫妙于砂壺,砂壺之精者,又莫過于陽羨。又云:凡制茗壺,其嘴務直,一曲便可憂,再曲則稱棄物矣。……星星之葉,入水即成大片。啜茗快事,斟之不出,大覺悶人。”李氏所談,可謂快語。
清中葉以后,砂壺之中,又重陳曼生(鴻壽)所制,名為“曼壺”。確較一般精雅別致。不過近來曼壺真者,頗不易得,即有價亦昂貴。日前在隆福寺古玩攤上,見有小砂壺一具,質式均極精巧,一入眼即知其必系名作,壺底果有“宣統元年匋齋自制”篆章,惜壺蓋略有殘缺,乃用漿糊粘合者。嫌其破損,太息而去。
返家后于心耿耿,終不能釋。乃于第二日亟【jí】去尋購,據云余看后即出手矣。按匋齋系清人端方號,端方好收藏古物。辛亥革命前,在四川被殺,其枕匣中只一部舊抄本《紅樓夢》。可見好東西自有識者。余所置雖有砂壺數件,而日用者仍為瓷壺。老實說還是沒有這種真正的閑心逸情,所以雖然天天吃茶,而沒有一次品茗。所謂品的環境與機會,也確是很難得的。